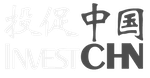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其中的礼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政府参与甚或主导的祭祀孔子、轩辕黄帝等的大型礼典几乎每年都在举办,民间自发的各种礼学实践活动(如汉服热)更是蓬勃兴盛。
可以说,“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核心之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心理、情感表达与行为习惯等等,都是通过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礼乐形式来养成并呈现的。博大精深的中华礼乐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时间的沉淀,逐渐形成了系列文字记载,其中既有关于礼乐起源、本质、精神等方面的讨论,也有关于礼乐仪式、器物、制度等方面的描述和记载。这一系列的文字最后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这三种典籍。“三礼”不光是对我国先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礼乐的文字记载,其思想内容也是我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绝对不容忽视的重要构成部分。
《仪礼》原名《礼》,是记载古代礼制的著作,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版本共有十七篇。汉代学者以其内容为士大夫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基本礼节,所以就称之为《士礼》,又叫《礼经》。晋代人认为其所讲的并非礼的意义,而是具体的礼仪形式,所以就称之为《仪礼》,并通行至今。《仪礼》主要记载古代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从成人、结婚到丧葬的各种礼节,及其交往、燕飨、朝聘、乡射、大射等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礼仪规范。历朝历代礼典的制定,大多以《仪礼》为重要依据,可见其对后世社会生活影响至深。
《周礼》主要是对官制展开的系统设计,是在汉代才被发现的一部“古文先秦旧书”。起初《周礼》的名字叫《周官》,西汉时期刘歆才将《周官》改为《周礼》。据《汉书》记载,《周礼》是河间献王从民间收集到的先秦古籍,献王将此书献给朝廷,却没能得到认可。直到西汉后期,在刘歆和王莽的推动下,《周礼》被列于学官,后来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又专门为之做了详细的注解,《周礼》才得到高度重视。
关于《周礼》的成书,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但《周礼》是一部性质特殊的著作,它通过三百多个职官设计组合成了一个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国家政权模式,这样一种完整而统一的模式应该不可能是出于多人之手。如清华大学的礼学专家彭林就认为:“《周礼》有缜密的结构、主体思想多元而一体,它只能出于一人之手。”但《周礼》究竟出于何人之手,迄今似乎仍难有定论。
《礼记》有《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两种,作者分别是戴德和戴圣,两人为叔侄关系。《小戴礼记》更为通行,今天我们所说的《礼记》通常就是指《小戴礼记》。《礼记》中的“礼”指的是《仪礼》,“记”是指对礼的经文所作的解释、说明或补充。《礼记》是一部先秦至两汉时期儒家学者关于礼学思想论述的文献汇编。它的内容庞杂丰富,综合了儒家传统礼学的各个方面,既阐释了《仪礼》所载各种礼仪制度的意义,也点滴记述了夏、商、周三代所传之礼,还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关于礼的一些问答与阐释,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学思想的重要资料。《礼记》既可与《仪礼》《周礼》相互补充,又可相互印证,是“三礼”中对后世影响较为重大的一部儒家关于礼学的代表性著作。
传统礼学有着丰富的哲学与伦理学思想,构成了中华礼乐文化与文明的基本内涵。礼学思想的发展,历经了漫长的过程,也离不开不同朝代思想家的努力。
《礼记·乐记》中说:“乐至则无怨,礼至则无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又说:“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将礼乐合称,并视二者的合而为一是经纬天地、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对此,南宋史学家郑樵就曾明确地指出:“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乐略·乐府总序》)在六经之中,礼与乐始终都是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我国古代的礼经与礼经学的一大特点。虽然自战国以后,乐作为经的一种已经基本失传,但仍然有部分内容遗存在礼经之中,并随着礼经一道流传下来。
自原始礼乐形成之后,到了西周与东周时期,礼乐具备了更为显著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而“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 (《孔子世家》),因此孔子对礼乐的整理和完善不遗余力,虽说是“述而不作”,但这个过程却仍是一个创新性诠释与重构的过程。孟子与荀子(主要是荀子)接过了孔子的工作,但更多的是对礼乐的意义和社会功能进行理论的诠释与完善。他们对礼乐这一文化载体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中,体现出了先秦儒家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各个方面的哲学观照与体察,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精神超越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子及学派也从自己的理论视野和关注重心出发,于三代礼乐传统作出了新的诠释和理论重构。至此,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对礼乐的论述和发挥,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哲学与伦理学蕴涵。
在两汉时期,学者们对儒家经籍的大规模训解、阐释和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字的繁琐训诂,并无太多高明的哲学性思辨与探索。到了两宋,中国哲学史上的又一个巅峰阶段,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们对礼乐本身所内蕴的哲学思想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与论述。这一演化过程既对理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又对礼乐本身的哲学意蕴做了部分消解、重构以及重要补充,丰富并扩展了礼乐内在的哲学体系。传统礼学经过两宋时期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具备了更加丰厚的哲学与伦理学的底蕴,对于自先秦以来的华夏礼乐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事实上,在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里,我们关于传统礼乐文化的态度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而现代新儒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在这方面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如牟宗三就认为:“中国文化,从其发展的表现上说,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这整个文化系统,从礼一面,即从其广度一面说,我将名之曰:礼乐型的文化系统,以与西方的宗教型的文化系统相区别。”(《中国文化之特质》)他较为充分地注意到了华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民族性,并准确地从“广度一面”名之为“礼乐型的文化系统”,确认了礼乐在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
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礼仪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这一现象反过来又刺激了一批学者加大对我国传统礼乐文化展开研究的力度,以期能够将传统礼仪和现代文明很好地结合起来,真正提升我国民众的礼仪文明素养。人们把目光也投向了具有数千年文明积淀的传统礼乐文化,希望通过推陈出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兴起“国学热”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