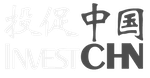美国亚洲历史学会列文森奖获奖作品《帝国之裘》利用了大量满蒙文献,在对东北和蒙古环境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皇帝对于北部边疆的想象、进贡体系与自然环境的恶化、清朝的奢侈品贸易和消费等诸多因素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提供了一种理解清朝边疆历史别样的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张永江、夏明方在北京大学博雅讲坛,对这一新的叙事方式展开了讨论。
一段物品的环境史
在清帝国,不能把人和毛皮分开。这是因为,服饰能够代表人的身份,毛皮尤其象征了满洲人的身份。更重要地是,在中国,毛皮代表着野蛮,而与毛皮有关的政策折射着帝国对外国和边疆的策略……
在本书作者、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谢健看来,早期现代中国,物质非常重要,人们比以往更多地思考、记录和关注商品。同样,在清帝国的世界中,想了解边疆或任何地方,就得认识那里的物产。
于是,本书将裘皮、人参、东珠这些清代贵族追捧的“奢侈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揭示了1760年~1830年之间满洲、蒙古地区出现的环境变迁。当时一股史无前例的商业扩张和自然资源开发热潮彻底改变了中国内地和边疆的生态环境,其中还伴随着动荡、对环境的焦虑和危机意识。
森林里的貂、狐狸和松鼠消失;野生人参被采光;采菇人把蘑菇连根挖掉;淡水蚌无法孕育珍珠。于是,朝廷千方百计地试图让满洲大地恢复原始的状态:征召士兵、设立卡伦、绘制舆图、注册人口、惩罚盗猎盗采者、调查贪污案件、改革官僚机构。官府还夷平参田、突袭采菇人地营地、设立无人区,甚至“肃清”蒙古草原……
你以为这是清帝国在保护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吗?作者认为,这实则是政府在“创造”一种新的环境。
过去,大多数历史教科书都把自然环境设定为一种背景或者原始的状态,谢健指出,在这样的叙述体系中,中国边疆地区就没什么特殊性可言了,它们就是汉地的一部分。
“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汉人的历史。”他认为,中国环境史研究采用“中国中心”而非“汉族中心”的范式,可以把中国内地和边疆的历史连为一体。
大历史的书写方式
“《帝国之裘》通过物的流动,把清代的商业、风俗、社会风尚、礼仪、族群关系以及政治统治等问题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背景非常丰富、延展性非常好的一个论域。” 张永江评价道。
他指出,目前国内针对边疆史的研究,尽管已经在边疆政策,族群专史,民族关系,民族地区的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有了很多成果,但它们的研究范式都比较单向。“很少有这种综合的、立体的、多向度、跨越多知识领域的鸟瞰式的研究。比如说蒙古史领域,至今没有关于蒙古环境史的著作,研究论文也很少见,少量涉及环境、生态问题的也不够深入。”
夏明方则提到了当下国内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研究受到地方史、区域史的影响,逐步走上地方化的道路,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家普遍感受到的碎片化过程,从宏观层面来说失去了说话的底气。”
在他看来,好的地方史、区域史研究从来不是碎片化的,而是通过对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某一个社会史个案的研究,形成自己相对比较宏大的关怀。
“作者把商品放在了整个的‘大清国’的范畴来讨论,而这个‘大清国’又和所谓的“内亚史”联系在一起,并延伸至欧亚,乃至全球。贸易导致物的流动,物的流动引起各种文化、族群、国家等关系的卷入,结果呈现的是一幅颇为复杂、相当宏大的历史画面,所以这是一种大历史的书写方式。”
夏明方表示,有一种说法可以形象生动地概括这类研究——“全球地方”。通过全球看地方,通过地方看全球,把全球和全球的关系、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通过选择某一个研究对象充分展现出来,这样,碎片化就不可能存在。
张永江分析,造成这种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料的缺乏,也不是语言障碍。“我们欠缺的可能还是问题意识。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不同领域、知识和理论研究的意识,或者说学术想象力。当然也缺少跨越众多学科的知识储备。这是我们学科教育和训练的不足。”
“新清史2.0”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批以清朝历史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以美国为主。他们关注的历史话题、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作品被统称为“新清史”。
张永江介绍说,美国的新清史研究有自觉更新的传统。
第一代新清史学者关注的是政治问题,他们从传统的政治视角包括权力、正统来研究清史。它的核心问题涉及内陆亚洲和中国的关系、内陆亚洲的族群和中华民族的关系,以及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的关系、是否可以等同……这种视角曾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
而以谢健为代表的第二代新清史学者,则把注意力转向了更加专门的领域,比如,他研究的是环境,是以商业网络为纽带的经济联系。这些研究的共同性在于,关注边疆的独特性,也就是边疆与中原的差异。
不过,在他看来,这本书的底色还是影射了边疆和内地的关系,或者说是内陆亚洲和中国的关系。
“新清史”很多研究者特别强调利用非汉文文献,然而,他们的文献虽然标榜是非汉文,实际却被指大多还是汉文或者二手材料。《帝国之裘》的一大研究特点,是用到了大量满文、蒙文的原始文献。
张永江认为,清史前后跨越将近三百年,地域也足够广大,因此情况千差万别,不能笼统地说非汉文文献就一定比汉文文献重要,这要根据研究的具体对象、问题来决定。
“研究边疆问题必须要用边疆民族的文献,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要知道,非汉文文献的传世和使用,并不是非常系统和连续的。清代,满文的使用在东北可以延续到很晚,可在其他地区,清中期以后就慢慢被汉文取代,或者是‘满汉合璧’了。”
他指出,如果刻意强调只用非汉文文献才能研究边疆问题,容易造成缺失。比如,作者给出的史实、展示的材料,在书中作为论据是比较薄弱的,因为他回避了汉文文献中那些更重要的事实。“我觉得,要依自己研究问题的需要来判断依靠汉文还是非汉文的文献,或者两者兼顾来使用也许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