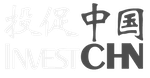豫中乡间,农人把学名叫兵豆的豆类,唤作扁豆或小扁豆,它和同是偶数羽状复叶的豌豆、蚕豆一样,都属于豆科蝶形花亚科野豌豆族。扁豆这个小名,很准确,四周扁平,中间微鼓,如果放大许多倍,模样形状像极了体育比赛中投掷的铁饼,或者乡间巧妇炕的烧饼。兵豆这个学名,很独特,大气别致,让人不由想起撒豆成兵这个成语,有种驰骋疆场的豪迈。我所知道的众多植物,名字中带“兵”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在我幼时,祖父曾经给我说过一个谜语:“一棵树个子低,春秋栽种都可以。等到果实成熟后,焦香烧饼最稠密”,谜底就是扁豆。扁豆棵低矮,籽粒小,乡人通常在扁豆前面,加个“小”字,谓之小扁豆,这个叫法很形象,扁豆是豆类家族中真真切切的小不点。有人觉得扁豆像鸡子的眼,就给它起了个绰号叫“鸡眼豆”。豫中乡间有两个老少皆知的歇后语,一个是王八看绿豆——对眼哩,还有一个是老母鸡叨黑豆——对眼哩。黑豆是黄豆的孪生弟兄,一身黢黑,更像鸡眼。乡人没有把黑豆叫做“鸡眼豆”,而把这个外号给了黑豆的“表兄弟”扁豆,个中原因或许只有常年和庄稼打交道的老农才知道。
扁豆是杂粮,属于粮食作物中的小众和陪衬,田边地头房前屋后,多少种上一些,不管收成好赖。在边角薄地,种其他作物,十年九不成,但种扁豆,多多少少都有收获,最不济也是种“一葫芦打两瓢”。按说,扁豆茎秆低矮,高不盈尺,是无法抵御风雨侵袭的。但事实上恰恰相反,扁豆这个身体羸弱的“袖珍姑娘”,却超乎寻常的皮实,脚踩牲口踏,车轱辘来回压,受尽诸多折磨,仍能顽强生长。
扁豆可春播,也可秋播。旧时豫中乡间,多为秋播,寒露前后,和小麦、大麦、豌豆、油菜同时播种,来年小满时节,提前于小麦、大麦两种作物,几乎与豌豆同时成熟。扁豆耐旱惧涝,多种在山冈地,与其他作物间作套种或混种,春播主要与大豆、谷子为邻,秋播多与小麦、油菜、豌豆作伴。扁豆籽粒小,不易顶破地皮,无论耧播,还是点种,都宜浅不宜深。祖父祖母在世时,我们家的几块薄田里,每年种麦时候,总要套种一些扁豆或豌豆。农历四月初,扁豆和豌豆这对姐妹,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几乎同时开花,豌豆的紫花,扁豆的白花,交织在一起,随风摇曳,给一地麦苗增色不少。祖母常念叨,年馑时候,要不是地里的扁豆苗和豌豆秧,一村庄的人可咋活命哩。祖母口中的扁豆苗,就是扁豆长到一拃长时的弱小秧苗。早春时节,饥不择食的庄稼人,为了果腹充饥,拽叶子,割秧苗。扁豆苗和豌豆秧是上天恩赐的救荒之物,就像韭菜一样,割不断,吃不尽,施舍饥民,拯救苍生。以至于许多年后,吃穿不愁的祖父祖母,仍忘不了当年小扁豆的大恩情,每年都要种些,心里留些念想。
乡谚说:扁豆开花二十八,豆面饼子噎嘴嚓。扁豆开花后,再过二十八天,基本上就熟了。扁豆种得少,割下来,通常都摊在场上,用长木棒捶打脱粒,再趁风扬去豆叶、豆荚,晒干磨成面,可以当口粮,度春荒。旧时年月,庄稼产量低,所获远远不够一家老小吃。粮食不够野菜凑,地里长的荠菜白蒿面条菜,树上结的榆钱槐花枸杞芽,但凡无毒能入口,皆可蒸煮当饭吃。除此之外,便是种些早熟早吃的作物,譬如大麦、豌豆、扁豆,填补小麦成熟前这段难熬的缺粮空挡期。
扁豆磨成的面,太干,没有油,无论是烙成馍,还是炕成饼,都不好吃,涩涩拉拉的,像吃沙子,很难下咽。幼时在乡下生活,每次吃扁豆面馍,我都站到水缸前,一手拿干馍,一手端水瓢,吃口馍,就口水。困难日子,有口吃的,不饿肚子,已经很满足了,谁也不会计较口感和味道,也正应了那句老话“饱时肉是粘的,饥时糠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