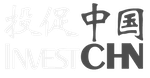2018年的中国经济释放出诸多积极的改革信号,其中个人所得税减免和专项抵扣便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成果。通过税的“减”与“退”,增强百姓获得感,让改革举措得民心。2018年改革实施首月,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提升至每月5000元,全国个人所得税减税316亿元,有6000多万税改前的纳税人不再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2018年10月领取工资薪金所得在两万元以下的纳税人,减税幅度都超过50%,占税改前纳税人总数的96.1%,减税金额达224亿元,占当月总减税规模的70.9%。
2019年,子女教育、房租房贷、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并扩大中低档税率级距落实后,全年预计减税总额6600亿,是原税制下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一,是实实在在的税收红利。税制改革以后,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能力相应提高。
当前,提振居民消费已经成为“稳增长”的必然选择和社会共识。我国居民消费的现状是,高收入群体收入高但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无法满足消费需求。中低收入人群的持久收入水平不提高,各类消费刺激政策缺乏支撑。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持久收入,释放消费潜力,可有效刺激内需。
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普遍较大,“无形之手”难以带动低收入人群收入快速增长。通过政府的“有为之手”,大规模对居民进行现金转移支付是目前各主流国家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的有效手段。根据OECD国家经验,通过再分配政策使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下降0.2左右(从平均0.5左右下降至平均0.3左右),其中四分之一归功于个税抵扣和抵免,四分之三归功于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能有如此效果,主要是因为再分配政策使低收入人群获益程度远远高于其它人群。
我国再分配规模和制度创新上均存在短板,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不能得到有效调节。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测算,包括社保支出在内,我国政府对居民的现金转移支付仅占GDP的9.5%,远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的21%。当前我国对低收入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以“低保”制度为主,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传统救济、医疗救济等为辅,但额度偏低、覆盖面窄。
如何给居民大幅现金转移支付?避免福利依赖是关键。目前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就业奖励”的方式。大量研究发现此类政策有效地避免了福利依赖,福利和激励可兼得。
“就业奖励”即政府根据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的就业状况或劳动收入发放奖励,在不削弱其就业激励的前提下增加其收入。目前全世界至少有22个国家和地区正在实施此类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国家的“就业激励”以个税为抓手。如美国的劳动所得抵免、英国的“工作家庭税收抵免”、新西兰的“独立家庭税收抵免”等,均基于“负所得税”的理念,向高收入家庭征税,同时以税收抵免的方式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转移支付,即对于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家庭,不仅不征税,政府还根据收入水平对家庭进行不同程度补贴,为防止负激励效应的出现,补贴方案的设计保持家庭总收入(家庭收入+补贴收入)随家庭收入上升而上升。
因此,“就业激励”比本轮税改提高起征点和增加抵扣更进一步,对难以享受抵扣优惠的低收入人群,基于其收入进行补贴,即低收入人群的税率为“负”。如美国的劳动所得抵免,覆盖美国三分之一家庭,其中低收入家庭受益率最高。另外,“就业激励”也可以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波动,提高预期收入,增加消费。
本轮税改增加个税减免和抵扣等手段主要获益人群是中等收入群体,但规模庞大的低收入人群从此次税改中受益不大,如在专项抵扣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就业激励”,则可以大幅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提高他们的收入,大幅促进消费。
综上所述,2019年1月1日开始的个税抵扣体系为后期实施“就业激励”政策,即大规模针对中低收入家庭实施转移支付做好了前期的制度安排,这是真正值得期待的大变革,对中国经济潜在的影响力不容低估。
为探索和积累在中国大幅增加对家庭现金转移支付的经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团队在过去4年多的时间里,采用随机对照实验的方法,开展对低收入家庭劳动收入进行奖励和以提高落后地区教育质量为目标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实验,即“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和“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实验结果显示,两个田野实验项目对低收入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劳动性收入和学生学业成绩方面均有显著效果。
2019年,中国经济要逆流而上,必须解决痛点。减贫和缩小收入差距将是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关键。以个税改革为起点,进一步巩固、优化和扩大对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让有消费意愿的中低收入家庭有钱可花,中国经济遇到的很多困难也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