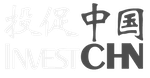人类,是与自然相分离的,还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并不是一个绕口令式的无意义问题,因为如果将人类界定为自然的部分,那么人的行为,哪怕是破坏自然的行为,都可以被界定为类似于火山爆发那样的自然行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让包括环境伦理学在内的伦理学成为多余。
但如果将人与自然相对立,就很难避免得出一个极性的认定,即将自然认为是人类生存的对立面。所以,一个合理的界定和区分是:人类与自然有着共生关系,但人的生活、生产显著有别于自然。这意味着,虽然我们受到自然影响,遵循自然法则,但反向行为可以是有益于自然的回馈,也可以是有害的。
环境伦理学是环境科学与伦理学融合产生的新学科,重在强调环境问题所涉及的价值观和原则。这门科学是在近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于自然界造成了突出影响,显现出人类生存发展活动和生存环境系统之间的严重对立后,为协调两者,确保共生关系的延续和改善而诞生的。
近日,英国哲学家、卡迪夫大学哲学名誉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伦理工作组前成员罗宾·阿特菲尔德所著的《环境伦理学》(牛津通识读本)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比较精炼扼要地追溯了环境问题和环境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探讨了环境伦理学相关的关键概念和相关的道德理论等。
环境伦理学作为学科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虽然蕾切尔·卡森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今看来不无粗疏和错误,但该书比较清楚地揭示了人类的行为尤其是战争和工业行为所带来的环境破坏。
讨论环境伦理学,绕不开一些基本的问题。生态环境的宣传活动中,经常会出现这类假想场景的破坏:设定工业和生活方式不变,若干年后的地球将千疮百孔,我们的子孙没有容身之地。这种场景的搭设目的,是唤起人们对于子孙生存前景的担忧,以同理心认同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的各种举措。罗宾·阿特菲尔德在书中说,对未来世代的关心其实从古至今,经由许多哲人阐发过。所以,我们也认为这种观念能够很好地产生效果。
然而,上述假设未必有效。比如,人们可以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潜力往往被大大低估了,生态环境的治理很可能取得了预期之外的巨大生效,或者说,新技术的诞生更改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淘汰了旧技术及其对环境影响。又如,具有相当科学基础的青少年,则可以从地球发展史的角度,了解宇宙运动对于地球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力量当然不是人类行为可比的。而上述地球未来糟糕场景的假设,则建立在宇宙运动、天体活动以及地球自身变化不存在的静止基础上,可以认为不是动态化的分析。
这也意味着,对于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理由,应当一方面更多地从环境伦理学中的义务论、德性论的视角,强调人与自然共生的契约性,强调人之所以为人,需要不断建构更好的自我;另一方面,基于功利主义论的视角,从现在出发,强调当世危害(可见、可验证),而不是过度依赖存在漏洞的未来估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