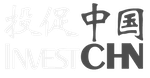不平等也有好坏之分。按照诺奖得主James Heckman的说法,凡是提高劳动技能报酬,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带来的不平等,应归于“好的”不平等。因为技能溢价的提高可以让劳动者有更强的动机去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产出。反之,凡是因为出生、外部环境、制度等原因而限制人们获取技能,以及限制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相应回报而产生的不平等,应该被归于“坏的”不平等。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与国企改革同步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很快。然而,不平等上升的原因为何,究竟是好是坏,却是值得我们认真审视的一件事情。在我与我的博士生唐高洁最新发表于《Economic Inquiry》的文章中,我们对中国1992年以来的家庭收入不平等发展趋势以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我们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辨析不平等上升的“好坏”之分。
数据与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使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1992到2009的年度数据。该数据是唯一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反映城镇住户各方面情况的大型调查。由于该调查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继续到现在,调查情况可以让我们看到城镇住户在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范围内的变迁。由于该数据独特的价值,基于该调查的学术研究也非常之多。
与许多其他研究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文献有所区别的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家庭收入的不平等,而不是个人收入不平等。由于家庭内部的资源共享及规模效应,家庭收入比个人收入更能准确度量福利。
研究方法方面,我们采用国际最新的收入分布的分解方法,将影响家庭收入的因素分为三类。其一是受教育程度。因为不同教育程度的个人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工资,婚姻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区别。因此,一国的教育程度分布是收入分布的基础。其二是劳动力市场因素,包括劳动参与,教育工资溢价,以及同等教育水平者内部的工资不平等。这些因素都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程度高度相关。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改革通常会提高教育溢价及增加同等教育程度者的内部不平等。其三是家庭因素。家庭因素又分为两类。一是单身率。二是已婚者夫妻之间的区配程度。家庭因素使得个人收入分布转化为家庭收入分布。
我们的分解方法可以将收入分布表示为一系列的条件分布。这样,通过控制某一个因素(条件分布)不变,而让其他因素随时间而变化,我们就可以得到在假设条件下的收入分布及相应的不平等指数。如果将假设条件下的不平等指数与真实的不平等指数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该因素对于不平等变化的贡献。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让中国的教育分布保持在1992年的水平,而让其他所有因素都变化到2009年的水平,我们就能算出假设教育程度不变的2009年收入不平等程度。这一指标与2009年实际不平等指数的差别,就是教育水平分布变化对于1992-2009年间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贡献。
不平等变化的趋势
关于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我们的发现与大多数研究类似。总体来说,1992年以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非常之快。根据我们的测算,1992-2009年间,中国城镇家庭收入的总体不平等基尼系数从0.266上升到0.407,上升比例为53%。如果用P90/P10,也就是九十分位数和十分位数的比例来衡量,收入不平等增加幅度更大,从3.2增加到8.6,增加了169%。此外,基于P50/P10衡量的收入分布下部的不平等程度比上部(P90/P50)增加更多。从各个地区来看,虽然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增加程度有所不同,特别是东北地区不平等程度增加较快,但各地区不平等上升趋势基本一致。
不平等变化的原因
我们接下来具体分析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具体原因。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大约可以解释家庭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四分之三。这些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这里面又有三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就业比率的下降。其二是教育回报的上升,也就是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平均收入的差别上升。其三是教育程度相同者的组内劳动回报差异的上升。我们发现这三方面的影响都非常重要,特别是教育组内不平等的上升对于总体不平等上升贡献更大。
其次,中国劳动力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对于收入不平等基本没有影响。 这一发现看似与许多以前研究的发现不一样。但一些研究常常把教育水平的本身与教育的回报混在一起。我们的研究将这两者分开,我们发现教育回报上升确实对不平等上升贡献很大,但是教育本身的分布变化却没有影响到不平等。虽然过去二三十年间,教育程度平均上升明显,但是教育的不平等状况却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只不过是整个分布向右移动。
最后,婚姻市场对于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大约贡献了四分之一。这主要是由于结婚率下降(单身率上升)引起的。家庭是共享收入和资源的单位,因此,单身率上升,特别是较低收入者的单身比例增加,无疑将对于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基于教育的婚姻正向匹配的程度有所增强,这一因素对于家庭收入不平等却基本上没有影响。这一发现也基本与美国一致。
好的不平等,还是坏的不平等?
从我们的发现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化以来的不平等增长,既有好的不平等,又有坏的不平等。考虑到改革初期教育回报的极度低下,教育回报以及教育组内不平等的上升,应该主要被归结于好的不平等。劳动参与率下降,以及单身率的上升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经济的因素,又有社会习俗文化变迁的因素。我个人认为相当部分还是因为人们拥有更多自由后,在约束条件下自主选择的结果。当然,低教育水平者因为缺乏工作机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中低收入者因非自愿的原因保持单身,这些都应该属于“坏的”不平等范畴。
综上,过去几十年不平等的上升,总体而言属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好的”不平等。也因此,我们应该欢迎这样的不平等增加。当然,目前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很高,诸多“坏”的因素蠢蠢欲动。例如,因为户籍限制和不合理的教育政策导致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问题,未来必将导致坏的不平等增加。为预防这样的情况出现,政府应该一方面在基础教育等方面更有作为,切实消除或至少减轻因为出生带来的地域,户口等因素带来的不平等,保证所有人享有公平的接受教育,获得技能的机会。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减少人口流动等方面的限制,进一步提高技能回报,增强劳动者获取技能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