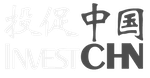夏日将尽,静安别墅红砖墙上的凌霄花仍旧开得热烈。
陶培青摘下老花镜,从衣料和针线堆里站起身来,走到弄堂口晒晒太阳,顺便活动几下因久坐而僵硬的腿脚。
“陶师傅,今朝生意好伐?”他笑着摆摆手。夏天是改衣服的淡季,“陶记改衣”店里不似往常忙碌,他才有空出来溜达。
几十米开外的“小黄改衣”门口,黄金玉倚在墙边,看着磨刀匠“霍霍”打磨她的剪刀。昨天,她手滑把剪刀摔到地上,刀刃立刻变钝了。一个裁缝怎能没有一把好剪刀?她赶紧打电话给相熟的磨刀匠。
“小黄”对面是“晓杭改衣”,往北走有“美美改衣”,与“陶记”并排的1025弄122号前院里,还藏着一家“122号改衣”。千禧年前后,这5家改衣店接连在静安别墅生根发芽,一晃就是20年,已经构成这片新式里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以前哪有改衣这个行当?我们都是做衣服的。”
“122号”店主张杰学裁缝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服饰多元之美的需求集中爆发。1985年,少年张杰离开家乡江苏泰兴,来到上海拜师学艺。
当时上海人家最流行的就是自己买好布料,然后请裁缝上门定制。张杰跟着师傅进过各色各样的家门,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吃喝都在那里。两个人,四只巧手,做好十来件衣服,一天下来能挣七八块钱。
他的同乡、“美美”店主赵建新的经历与之相仿。在数千趟上门制衣过程中,他们练就了一把量体裁衣、缝制整烫的好手艺。
随着赵建新在圈内的名气越来越响,一家上海服装厂老板邀请他到厂里从事管理工作。没过多久,他去了温州某家服装厂。2003年,他又前往杭州开厂。厂长难做,既要跑业务,又要管工人,加上“非典”冲击,赵建新很快便感到挫败。
这时,姐姐的一通电话救他于水火:“阿弟,你回上海帮我吧。”
他的姐姐也是一名裁缝,比他更早来到上海,“美美”店名就是取自她的名字。姐姐起初也以做衣服为生,然而到了世纪之交,她嗅到了不一样的商机。
从1997年到2001年,梅龙镇广场、中信泰富、恒隆广场三大商场陆续建成,南京西路商圈崛起。“梅泰恒”里的众多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门店,不仅为人们提供了“领行情”、开眼界的机会,还吸引着那些钱包鼓鼓的新一代消费者。
只是,由于不同人种体型差异,很多顾客发现自己花大价钱买来的华服美裳并不合身——明明尺码相同,袖子或者裤脚却长了一截,穿着很是别扭。店员注意到顾客的需求,主动替他们留意起了裁缝师傅。
也正是在1997年,张杰和陶培青已经立足静安别墅,开出了自己的裁缝店。商场店员中午到这里来吃小馄饨,恰巧遇上他们,生意就这样谈成了。从此他们纷纷转型成为改衣裁缝。每天,店员送来需要修改的衣服,他们加工完成后再送回去,由店员转交给顾客。
陶培青回忆,订单最多的那一阵子,共有28家店找他改衣。赵建新姐姐手里也有27家,实在忙不过来,把他从杭州叫了回来,另外还雇了两个帮手。
衣服数量多,店里又催得急,对他们来说,加班加点赶工是常态。陶培青经常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有时甚至趴在缝纫机台板上过夜,醒来继续干活。
凭借地理优势、精湛手艺和勤恳态度,静安别墅里的小店与“梅泰恒”里的大牌建立了稳定的关系。
“122号”的墙上至今还贴着那些品牌的标签:“博柏利”“杰尼亚”“范思哲”“登喜路”“阿玛尼”……张杰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小心地给一条“罗意威”的连衣裙拆线。
陶培青从工作台上随手拿起一块边角料给我:“你摸摸看,不一样的。”接着他翻出一条触感同样细滑的裤子,原来这块料子是从“古驰”裤装上剪下来的。这样的大牌服饰边角料在台面上到处都是。
“小黄”和“晓杭”虽是后来者,但受益于集聚效应,也分到了商圈的一杯羹,接到不少二三线以及快消品牌的订单。性格开朗、擅长社交的黄金玉迅速和商场店员结下了交情,订单如流水般哗哗而来。那是改衣裁缝们的黄金时代。
改衣服并不比做衣服简单。
黄金玉年轻时在上海西服厂工作,学了一手“推、归、拔”的功夫,自觉“科班出身”,手艺不输其他裁缝。但她仍然视改西服为苦差,“太麻烦了,要好好开动脑筋的”。
要动什么脑筋?陶培青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每件成衣都有不同版型,既要改得合身,又不破坏原来的版型,这才算好。”
比如改一件西服,首先要量准肩宽、胸围、腰围、袖长、袖围等尺寸,然后一点点把缝线拆除,在保留整体版型的提前下,按照顾客身材画样、裁剪,最后重新缝合。其中每一步都耗时耗力,一名技术成熟的裁缝需要两天时间才能改完一件西服。
再比如改小裤腰,并不是简单地剪开腰头、缝得更窄而已。改衣裁缝的做法是把从上到下的裤边缝线全部拆开,根据尺寸整体改小,再把裤边缝合起来。只有这样,改好的裤子才真正贴合人的身体线条。
“这叫推档。”赵建新甩出了一个专业术语,见我疑惑,又补充道,“就是等比例放缩的意思。”
在与大牌衣料、新潮设计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裁缝们的手工艺和时尚感也在不断提升。
张杰经手过一件针脚极其细密的大衣,用剪刀或者刀片都无法拆除缝线。他暗自思忖,也许国外的制衣大师本就不希望这件衣服受到任何改动。于是他只能用细针慢慢挑开每处针脚,再把它们剪开。
晓杭改皮草外套很有经验。他分析说,皮草的难点在于不能用缝纫机,全都要靠人工缝合,修改一件得花两周时间。做这一行就是这样,门槛不高,但是只有与时俱进、勤于思考,才能达到更高水准。
近年来,国产设计师品牌在服装界异军突起。“陶记”店里,陶培青正在修改一件国内小众品牌的女士西服。这是设计师本人拿过来请他调整版式的样衣。
“剪裁不够立体,版型太垮,显得没型……”他一口气数出了许多毛病。这样的西服称不上佳作,设计师也明白,所以要等老师傅陶培青改完,再拿回厂里依样批量生产——在审美和细节处理方面,陶培青已经超过了很多打版师。
如今,静安别墅改衣店的生意一半来自商场,另一半是直接找上门的顾客。顾客当中,既有服装设计师这样的行内人,也有时尚行业相关从业者。
黄金玉的一位顾客是时尚杂志《世界时装之苑》的编辑。她给我看这位客人的微信朋友圈,背景赫然就是一张他与香奈儿前艺术总监、“老佛爷”卡尔·拉格斐的合影。
“这么说来,我也算半只脚踏进时尚圈了。”烫了一头卷发、涂着玫红唇彩的黄金玉有些得意地说。
不过,更多顾客与时尚圈没有多少关联,拿来的衣服也不华贵。一条裤子,原价几百元,去找这里的任意一家店进行整体放缩,都要150到200元上下才能成交。这笔买卖听起来似乎不太划算。毕竟,裤腰大了用腰带束一束,裤腿长了卷两道边,都是不花钱就能解决的小问题,何必诉诸改衣?
在陶培青看来,原因就是两个字——讲究。他说,站在上海街头望去,哪怕白首老人,穿着打扮也不含糊。正当年的男男女女们,更是衣着入时,清爽得体。
对于讲究的上海人而言,衣服不一定要贵,但一定得是整洁而合身的。因为只有衣服合身了,人才更有精气神,所以经常光顾“小黄”的市民章女士说,改衣就是一种刚需,“没什么好奇怪的”。
时尚资源,讲究人儿,在改衣店里演绎着一幕幕“上海摩登”。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价位。
陶培青开始不愿意接受采访。一旁的陶太太快人快语,提起数年前也有记者前来采访,报道发出以后,许多新客慕名而来,但当听说改条牛仔裤要百把块后,有人就在消费点评网站上吐槽“黑心商家”“价格离谱”。
这让夫妻俩生了好一阵子的气。“先不说改衣服的工序多么复杂,他们知道这边的房租有多贵吗?”
“陶记”店内面积约为12平米,现在每月要交5000元租金。“美美”位置更好,两层楼共12平米,租金是7000元。“晓杭”租的是亲戚的房子,5平米的屋子只要1000元租金,看似便宜,但逢年过节少不了给亲戚送礼,实际租房成本也不算低。
除了黄金玉是上海人,其他4位裁缝都来自江浙。居大不易,我从不同人口中听到了同一句话:“开店容易守店难”。
这些年来,实体经济受到电商冲击,改衣店接到的商场订单比以前压缩了很多。同“美美”仍然保持联系的只剩3家门店。自姐姐去世后,赵建新就辞退了另外两位阿姨,独力支撑这爿小店。5家改衣店里,只有“陶记”还雇人做工,其他4家都是店主单干。
同时,以“易改衣”为代表的互联网改衣品牌正在加速发展。它们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改衣模式:消费者在线上下单,通过快递或平台方上门量体并收衣的方式,把衣服送到各区域中央改衣工作室处理。相形之下,传统改衣行业的经营优势变得更小了。
这些互联网改衣品牌努力把触角伸向实体改衣店。前两年,“易改衣”工作人员找到陶培青,拐弯抹角地向他了解静安别墅改衣圈子的情况。陶培青既不想透露内情,也无意加入互联网改衣阵营,这段接触就没了下文。
说到底,其实也没有多少内情。“同行是冤家。”除了张杰和赵建新是老乡,偶尔互相串门借点针线以外,其他人之间基本没有往来,只顾守着自己的小天地。偶尔从顾客那里听到一些评价,说某位师傅手艺不灵,他们都不吭声。就像张杰说的,“众口难调,管好自己的事吧”。
曾经积极投身时代浪潮的裁缝们,在面对新的浪潮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保守的一面。
赵建新的姐姐走了,但他希望“美美”留着;黄金玉自在惯了,不想回到管理体系之中;张杰和晓杭都是耐得住性子的匠人,也不乐意搬迁。他们和陶培青一样,都选择留在静安别墅,不去理会互联网改衣的风口。
陶培青认为,改衣店最大的危机不是房租,不是业务量在互联网冲击下减少,而是后继无人。去年疫情暴发以后,“陶记”停了三个多月的业。这段时间,他得以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长长的假期,便认真考虑起未来。
可是,思来想去只有“关门大吉”四个字。因为“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学裁缝了”。
这是整个裁缝业的危机。互联网时代能挽救这一行业吗?目前看来,结果仍是未知。
采访到了尾声,一位年轻男士推门而入。陶太太惊喜道:“小李,你好久不来了,最近在忙什么?”
“忙着谈朋友!”
店里传出一阵笑声。
小李此行的目的是要改小几件衬衫。由于健身卓有成效,他原先的衣服都不再合身,所以来找陶培青帮忙。
第一次来“陶记”时,小李还是一名大学生。8年过去,他的生活已经变了许多模样,与陶培青两口子的交情却越来越深。陶培青为他量体的时候,他熟练地配合前者的动作,两人宛如一对默契的舞伴。
每家改衣店都有这样的熟客。有人从自己少女时代开始改衣,到现在领着一个小小少女过来,让裁缝师傅修改女儿的衣服。改衣裁缝见证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成长。这些成长既有身体上的——量体时可以最清晰地感受到,也有精神上的——如果客人愿意交付心事,裁缝们也乐于倾听。
这是他们不愿搬离静安别墅的另一个原因。
陶培青的三十年,也见证了南京西路一带的巨大变迁。1990年,他从苏州来到上海。那时他已经是一名手艺过关的裁缝了,经人介绍到静安区威海路幼儿园工作,专门为幼儿园里的教师和学生定做制服、表演服等服装,从此在这一片扎下了根。
他还记得,当时延安高架还没修建,没有地铁,威海路还是远近闻名的汽车配件一条街。周末,他带着妻女去上海跑马厅参观,三个人挤在公交车上,晃晃悠悠地抵达目的地。
数年过后,延安高架中段工程启动,1号线也已经开通运营。有天晚上,陶培青听到“轰隆”一声巨响,是幼儿园附近工厂爆破的声音。
“工厂拆了以后,你猜建了什么?”
我摇摇头,他说:“就是你们文新报业大厦!”
静安别墅里的日子并非没有波澜。奶茶店,咖啡馆,理发店……这里开出的小店一度比现在多。但是这些商铺基本都没有营业执照,“陶记”等改衣店也是。
为了减少经营户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维护静安别墅作为历史优秀保护建筑的整体风貌,2010年开始,静安区相关部门针对“居改非”、无证无照经营等现象进行整治。到2013年,大部分违章商户都被取缔。
那段时间,小区里到处悬挂着“制止违法转租改建”“依法取缔无证无照经营”的横幅,陶培青等人为此忐忑不已。好在,因为改衣店扰民程度不高,兼有家庭作坊般的便民服务功能,最终被保留下来。
城市管理中的温情片段,就此被记录在了改衣店的生命史上。
尽管仍有许多困境摆在眼前,甚至自嘲“难登大雅之堂”,比不得上海著名的红帮裁缝,静安别墅里的改衣裁缝们,还是靠着耐心、专注和坚持,赤手空拳在大城市闯出了一片天。他们的子女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回到上海工作,方便照应父母。
这样司空见惯、却又屡屡令人感动的家庭奋斗历程,真实存在于城市变迁的缝隙里,留在时间密密麻麻的针脚里。